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自我审视——刘易斯·温菲尔德和他的福州故事

英国旅行家约翰·汤姆逊镜头中的福州女性(187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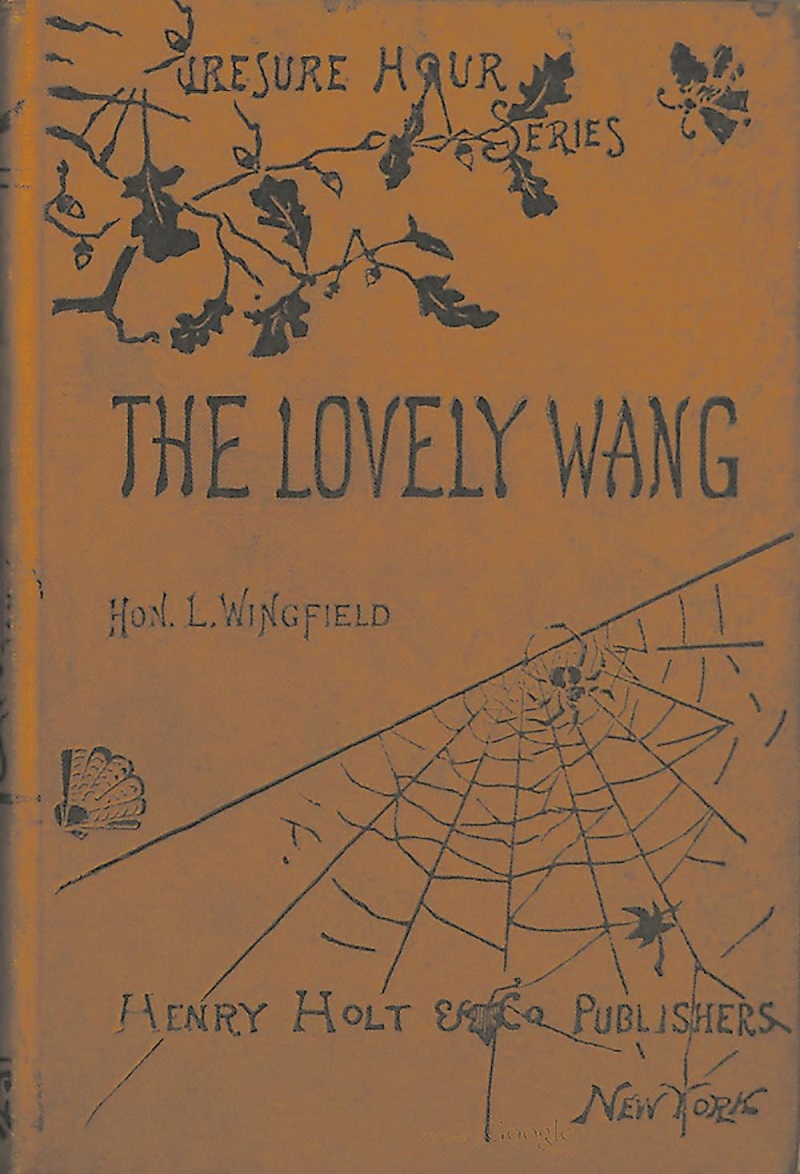
《王家女公子:中国小记》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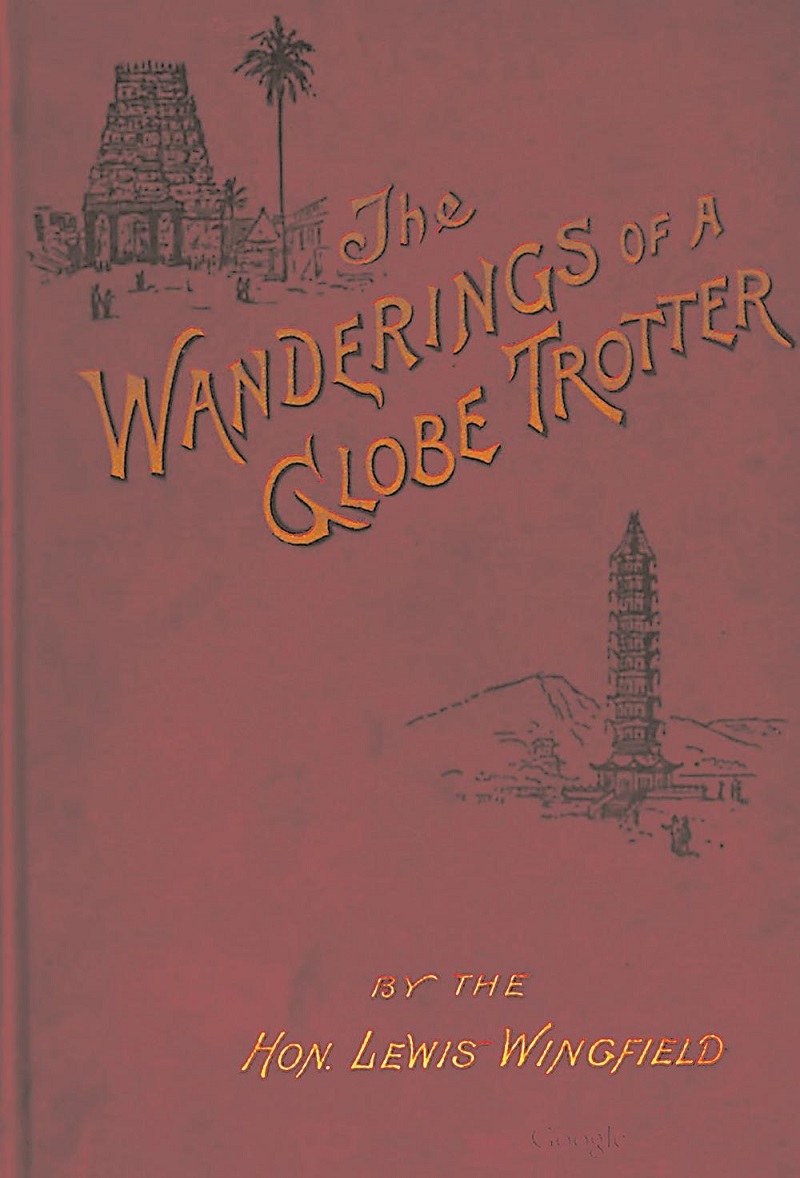
《一个周游世界者的远东漫游记》封面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福州开埠,福州成为晚清重要的对外交流窗口。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人、传教士、使节和旅行家接踵而至。他们对这个“风景如画的港口”极感兴趣,留下不少和福州相关的书写。
小说家刘易斯·温菲尔德(Lewis Wingfield 1842—1891)在1887年出版以福州为背景,讲述福州人故事的中长篇小说《王家女公子:中国小记》(The Lovely Wang: A Bit of China),该作214页,塑造出一位晚清封建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小说叙述者“我”是中国人,叙述者和作者国籍不同、各自独立;叙述者站在晚清中国的立场,称传教士或英国人为“野蛮人”(barbarians)。
温菲尔德其人
温菲尔德出身于伦敦的贵族家庭,求学于伊顿公学和波恩大学。和同时代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一样,温菲尔德具有冒险精神,其职业生涯跌宕起伏。
他在伦敦的剧院当过演员,做过外派记者报道普法战争,然后专注于绘画,画作亦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艺术展上展出,后来成为剧院的服装设计师。40岁左右时,他开始小说创作,一生创作出大约10部长篇小说。
他的创作方式也颇有个性。一般而言,小说家都喜欢远离康拉德所谓的“破坏性因素”,在隐居状态下创作;偶尔会有少数小说家愿意近距离接触这些因素。但是,没有哪位作家像温菲尔德如此肆无忌惮地投身于这些“破坏性因素”。
《牛津国家人物传记词典》这样描述:“温菲尔德行为古怪,比如装扮成‘黑人吟游诗人’去德比赛马会、在济贫院过夜、和流浪者一起露宿以及在疯人院当服务员等。”
对他而言,生活体验对文学创作必不可少。他的两部和东亚有关的小说体现了这种创作观。1886年至1888年,他游历晚清中国和日本,成为一个“周游世界者”,然后创作出《王家女公子:中国小记》、《越生的诅咒:古日本记事》(1888年)两部小说和散文作品《一个周游世界者的远东漫游记》(1889年)。
此游记中有两篇与福州相关,第一篇是《永福寺》,记述作者游览方广岩寺;第二篇为《福州医院》,记述一位苏格兰医生在中洲岛建立一家西式医院,给福州人实施一些小手术,但医院最后却被纵火者烧毁。
福州浪漫喜剧
维多利亚时代有关福州的书写,其中绝大部分是游记,比如探险家理查德·科林森的《福州府见闻》(1846年)、传教士施美夫的《五口通商城市游记》(1847年)、传教士兼汉学家麦都思的散文《鼓山》(1855年)、英国旅行家兼摄影师约翰·汤姆逊的插图游记《福州和闽江》(1873年)以及一位匿名作者发表在文学杂志《一年到头》的《福州街景》(1881年)。
以福州为背景的小说较少。1875年7月,一位匿名作者在文学杂志《康希尔杂志》发表题为《建桥记:一则中国传说》的短篇小说。该作12页,讲述闽江万寿桥(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Ages)的建桥经过,其中前半部分是对观音菩萨化身少女募集造桥经费这个民间故事的改编。
1898年,小说家丽丝·波姆出版中篇小说《多布森的女儿:中国通商口岸故事》,该作72页,讲述英国茶商多布森的私生女沙嘉在福州的不幸遭遇。
《王家女公子:中国小记》则是一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喜剧小说,叙述了女主人王梅花(Plumbloom)的爱情故事——清乾隆年间,福州(Foochow,福州话拼音)闽江的中洲岛上有一位黄姓富商,膝下一儿一女。女儿18岁,儿子16岁,名黄楚。黄商人此时行商不顺,债台高筑,全家人把希望寄托在女儿和永福县(Yuen-Foo,即永泰县)王县令的公子王玉的联姻上,希望不久女儿嫁入王家,王县令能出手相救。
然而,王玉虽然才20岁,却沉疴难起,困于病榻。王县令无奈之下请求黄家把女儿送到王家,希冀王玉见到她能转危为安。形势所迫,黄商人准备送女儿入王家,但是黄夫人和黄太夫人坚决反对。黄商人自己也有所顾忌,就让贪玩厌学的儿子黄楚装扮成姐姐,和媒婆魏夫人去王家。
两人坐船沿着永福河(即大樟溪)来到王县令府邸。黄楚在见到王玉之前,遇见王县令的女儿王梅花,并对她一见钟情。王梅花娇俏活泼,性格像假小子。接着,黄楚见到卧榻不起的王玉,王玉此时病得有点糊涂,认为和“黄小姐”成亲可以冲掉晦气,决意留下“黄小姐”。但王玉病重难起,于是要求妹妹梅花到时替自己和“黄小姐”拜堂。兄意难违,同时梅花对这位没过门的“嫂子”也有莫名的好感,便应允下来……
全书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福州城为背景,介绍男主人公黄楚的家庭背景和黄家的困境,为情节发展作铺垫;第二部分以永福县为背景,叙述王梅花和黄楚的相识、相恋和错配婚姻;第三部分描写黄楚出逃王府、沦落京城,而王梅花知道真相后不畏艰辛、矢志寻夫,最后两人在福州成亲。
他者中的自我
《王家女公子:中国小记》的扉页上写道:“这部小说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以及那个国家贵族家庭的礼仪制度。”但对中国的认知是通过福州进行的。
温菲尔德笔下的福州形象,涵盖人物、服饰(新娘的红盖头)、器具(纸钱、香火、花轿和帆船)、工艺(白锡工艺品)、习语(称媒婆为白蚁、新夫人、苦力、马夫、寿枋、心头发毛和行将就木)、礼仪(拱手、作揖、跪拜和九叩)、餐饮(婚礼上的烤猪)、习俗(冲喜、缠足、重男轻女、卖身、已婚妇女盘发、烧香念经、过节祭祖、清明节扫墓和清官离任遗爱靴)以及地理景观,对闽江中洲岛一带、大樟溪沿岸的描写尤为细致。
此外,小说还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首先,小说具有进步的女权主义思想。就情节而言,小说和《醒世恒言》中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相似,都有“弟代姊嫁,妹替兄娶”的情节。但小说展现了一个不囿于世俗道德观念的独立女性形象,这种女性形象在当时晚清封建社会显得难能可贵。王梅花不惜违背传统的道德观念,也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呼唤,呈现出不向命运妥协的勇气。
小说多次强调王梅花的男性特质,叙述者通过王家的乳母这样描述王梅花:“她前身定是个男子,没在阴间待够时间,转世投错胎成为女子。深思熟虑之后,她终于醒悟,这就是问题的根源。这世上很多女子本应是男子,反之亦然。她的独立和活泼身不由己……不幸的是,作为女子,她聪慧过人。她又不愿嫁人为妻,这是可怕的污点。因为女子的第一义务就是出嫁。
“‘你多关心王玉吧,’梅花总是这样恳求,‘让我听天由命吧,适合我的男子必定与众不同,也许我永远也找不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位女子竟欲主宰自己的命运,这可能让人震惊。但我就是生而如此——谁都改变不了这点。或许我前身是一只海鸟、树上的松鼠或者蒙古山脉上的野山羊。’”
王梅花女扮男装,在茫茫人海中寻夫的情节,更让人见识其为爱情表现出来的无畏与勇敢。温菲尔德对晚清女性和爱情的歌颂,与同时期英文作品中把晚清女性描述成深闺妇人截然不同,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中国女性观。温菲尔德似乎在晚清社会看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伴侣式婚姻”——婚姻以自由意志和爱情为基础,而非是获取经济好处或提升社会地位的权宜之计。
其次,小说的非殖民主义叙述。19世纪后半叶,不列颠帝国急剧扩张,殖民地遍布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同时,英国对晚清中国的政治制度、传统宗教、伦理思想和社会习俗更加蔑视。于是,当时以晚清中国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常常以海上劫掠、神秘宝藏以及清朝酷刑为话题。
一些英国小说家,比如乔治· A·亨提、哈利·柯林伍德以及威廉·C·达维都大力宣扬英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并对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扩张表现出极大热情,他们将晚清中国作为大英帝国的据点之一,在这些据点上嫁接他们的小说。于是,这些小说基本上都带有殖民主义色彩。
《王家女公子:中国小记》则无此缺点。这从小说的情节、主题和人物塑造可以看出,也体现在小说独特的叙述方法。大多数此类小说和游记用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是异国人,叙述者和作者文化同源、合二为一,把晚清看作一个“异托邦”。《王家女公子:中国小记》的叙述者“我”却是中国人,这种叙述角度的改变看似平淡无奇,其实说明英国人对晚清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有个漫长的嬗变过程。此时的认识达到新层次:他们开始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自我审视;通过这种自我审视,他们其实进一步认识了晚清。
托马斯·G·塞尔比,一位长期在广州一带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在1901年出版著作《中国人眼里的我们》(As the Chinese See Us),也是由英国人站在晚清的立场进行自我审视。
(作者单位: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福建日报》2022年2月22日 第12版:理论周刊· 文史



 闽公网安备:
闽公网安备:


